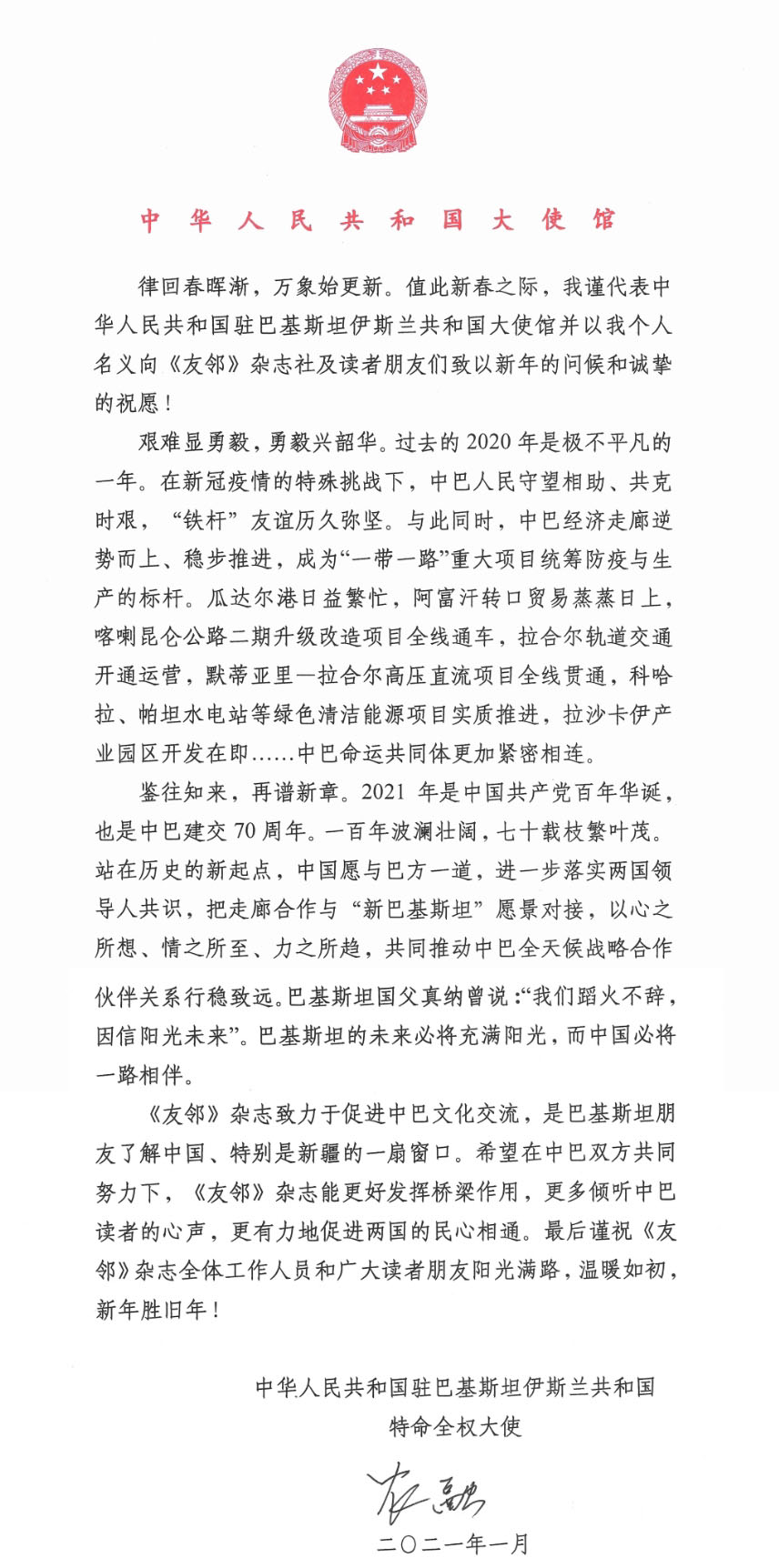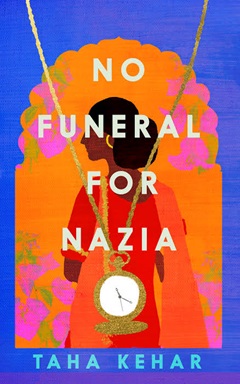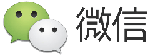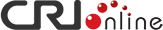阿瑞布.阿沙哈:人类灵魂的游吟诗人
作家: 伊曼•阿姆贾德 - 发表于: 2013年10月22日 | ENG (English)

眼前这位身穿淡蓝色衬衫,一手捏着香烟的卷发男子,淡然地谈起他人生中经历的那些将他塑造成阿瑞布•阿沙哈的阶段:左翼政治斗争的产儿,幻灭的社会主义者,来自萨格勒布的流浪歌手,胡斯-内-哈奇奇可乐工作室的主播,以及人类灵魂的行吟诗人。
阿瑞布步入聚光灯的生涯始于他接到可乐工作室建筑师罗黑里•哈亚特的电话的那一刻。后者听过阿瑞布的音乐并很希望听到更多的新作品。阿瑞布说:“能成为可乐工作室的一员是很令人开心的。”因为它给他的印象是很专业,并且尊重音乐人。他说道:“每个艺术家来到这儿都备感亲切和受欢迎”。他认为这才是可乐工作室成功的原因。他还提到:“他们明白真正的音乐的价值,明白将其融入更华丽的文化背景里,将会给城市听众带来值得注意的多样化的音乐”。
但在可乐工作室的名声影响他之前的几年,阿瑞布的歌曾是以社会主义题材为主的,如法伊兹的诗歌和工人阶级运动。 他早期的作品基本都以民歌曲调和绍卡特•阿里, 图费勒•尼亚孜和阿勒姆•拉哈尔这些经典声音为主的,因为那时他的父亲正在建设巴基斯坦国家电台PTV。当阿斯拉姆•阿扎尔在齐亚•吾哈克时代流离失所时,他们全家搬到了卡拉奇。尽管巴基斯坦的第一个电视台是他临时的家,但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认同感。
 |
这位年仅17岁的的社会主义者前往莫斯科去寻找共产主义,平等和阶级意识,但他面对的却是理想的幻灭。腐败和绝望的苏维埃政府,只不过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泡沫理想。尽管许多人仍然抱着人性和变革的理想,但是社会制度令他们失望。阿瑞布于是对所有的“主义”都失去了信念。他意识到唯一值得为之奋斗的真理和意识形态只有“人性”。在莫斯科时,他与一对南斯拉夫夫妇成为朋友,他们说服他回到能够提供最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
那1990年,一年后南斯拉夫的民族难题导致残酷的内战和国家瓦解。在欧洲这场自二战之后最致命的战争期间,阿瑞布重新弹起他的吉他,就好像那些社会主义运动期间的卡拉奇街上的少年一样弹奏,但他不是为任何“主义”而弹奏,而是为了人性的希望。 他只是一个在街上,酒吧和餐馆,同不同的组合和音乐家一同演奏的普通人。 后来,他同一名爱尔兰人,一名巴基斯坦人还有克罗地亚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名为“沙姆罗克流浪者”的乐队,兼收并蓄凯尔特人和爱尔兰人音乐。“沙姆罗克流浪者”辗转东欧和中欧的酒吧演出了七年。 阿瑞布爱上了那里的欣快,美丽和人民。他在他的第二故乡克罗地亚住了13年。
 |
阿瑞布最初搬那里是去学习哲学和印度学,这给了他研究这片土地的古代文化的机会。他一度沉浸在“吠陀经”,佛教,锡克教和梵文文本的哲学教义中,但最终音乐使他放弃了完成学位。 他承认他在学术界短暂的时间给了他一种自己的历史感。但阿瑞布从未真正放弃他的学位,因为哲学和古代典籍中的灵性总是会或多或少的体现在他的音乐的灵魂中。
在东欧的13年中,阿瑞布弹奏了各种类型的音乐,从吉普赛到南美到爱尔兰音乐。但最终,他越来越对“我们自己的音乐感兴趣,并决定回来钻研它”。他认为“ 我已经失去了和音乐元素的灵魂的接触,所以停止了作为艺术家的成长”。他重新审视了以民间文化为背景的音乐;当他挖掘到巴基斯坦遗失的诗歌和民间曲调是,他的音乐注意力开始向以人为本的苏菲•卡拉姆转移。他2006年的第一张专辑《瓦基》, 由八个音轨组成,使用了《卡瓦伽•古拉姆•法理德》,《布勒•沙》,《缅•穆罕默德•巴克什》作为歌词,甚至还有现代诗歌《萨尔玛德•塞白》。然而他反对自己困在苏菲派里。他说“我已经被匪类成年轻一代的苏菲音乐家。也许还是一个用更简单的方式去神化全球的音乐家。但我从未自称是苏菲音乐家;对苏菲主义每个人的理解方式都是私人性的”.对他来说 “主义” 并不重要;苏菲诗歌关注的是发现的过程而非结果。对于他来说,苏菲主义的哲学通过苏菲的诗“是超越宗教的,或者是连接全人类的真正的宗教。”
对于阿瑞布来说,音乐和哲学是和谐的,但对于一个挥舞着音乐产业的国家来说,音乐家们需要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及其根源。他说:“我希望从我们开始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我希望这类音乐能够触及更广泛的听众和更多的街头听众”。阿瑞布的音乐灵感不仅来自他读的诗歌,他踏过足迹的地方和他听到的乐器,更来自于他对人类灵魂价值的理解。这个蓝衬衣的男人熄灭他手里的半根烟头,思考着说到:“我挣扎着,我作为一名艺术家挣扎着生存。艰苦的工作开始初显成效,这一路非常艰辛”。正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挣扎时的诗性智慧和永恒歌谣 能够协调,并创建了一个不容于任何框架和流派的民族音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定义阿瑞布•阿扎尔的原因:“一位人类灵魂的行吟诗人”。